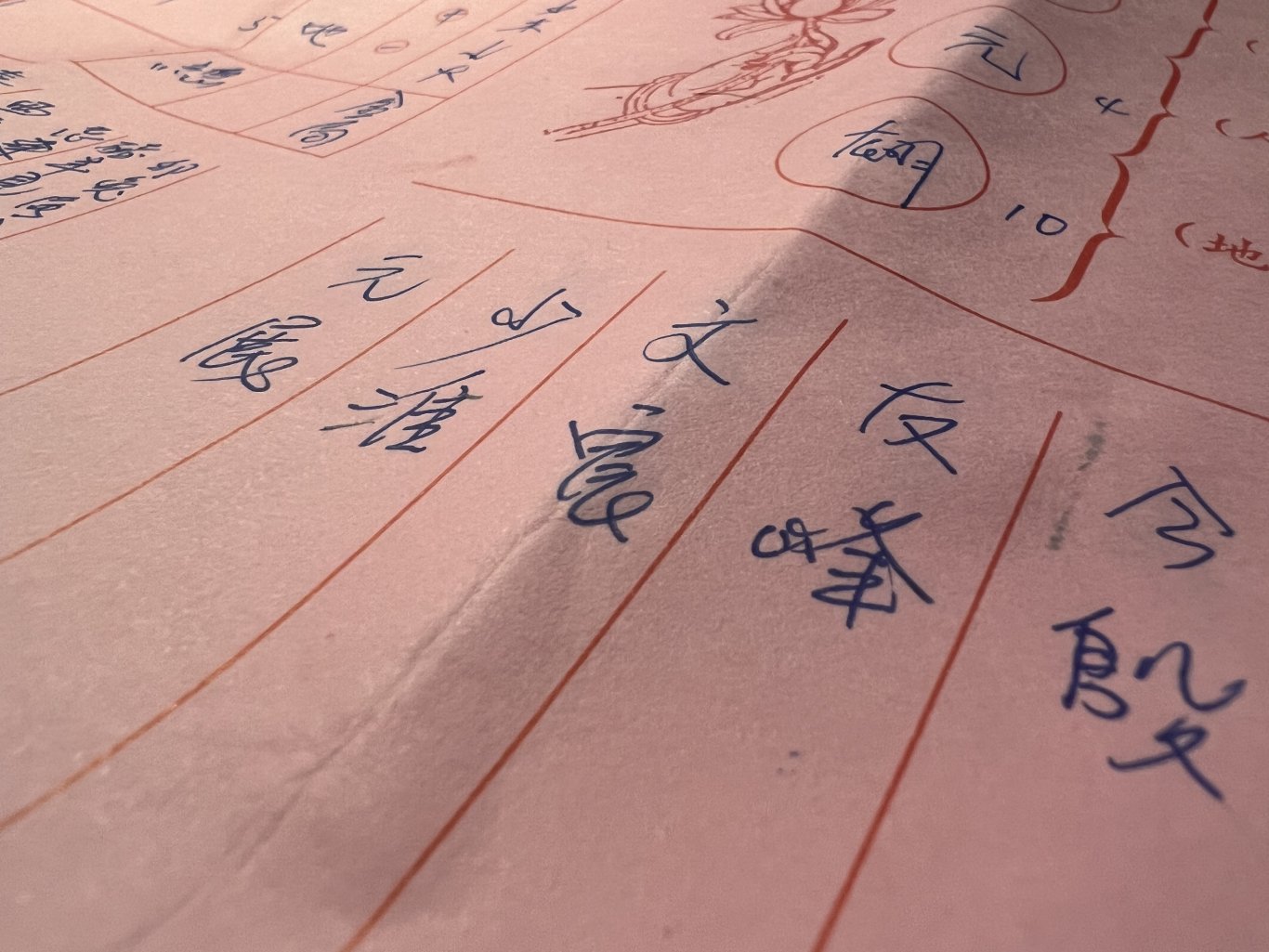總有人問我,為什麼叫少淮,這又不是本名?
我從不解釋。
有時候笑笑說:「順口啊。」
有時候隨口回:「就隨便取的。」
但其實,那天選這個名字時,我心裡很清楚,有些事,就算來不及了,也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0
如果可以,我當然也想要完整的東西。
完整的家、完整的童年、完整的自己。
但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
有些人天生就少了點什麼,有些事從一開始就來不及。
像是缺席空出的課桌椅,某些不曾叫起的稱呼,某些怎麼也拼湊不出意義的過去。
有時候我會想,人生是不是就是這樣,一直在錯過,一直在丟失,然後不知不覺就走到了現在。
#1
奶奶常說,我姓謝,是謝家的人。
可我總覺得,這句話裡少了點什麼。
這句話像影子,在陽光下清晰筆直,夜幕降臨時,卻悄然消失。
它存在過,但只有在特定的光線裡才看得見。
有些人即使共享同一個姓氏,卻始終站得太遠,像是在履行某種形式上的親情,卻從未真正靠近過。
相比之下,外婆家的人從來不說這種話。
但在某些時刻,我還是能聽見那些刺耳的話,像筷子輕敲碗緣的聲響,不大,卻總能讓人聽見。
有時是一句不經意的玩笑,有時是一聲似笑非笑的感嘆,落在話語的縫隙裡,不重,卻無法忽視。
我在這兩個地方之間擺盪,像是短暫歸屬於哪裡,又不屬於哪裡。
就像風起時,沙粒會被捲入,看起來沒有分別,每一粒都與彼此交錯,短暫共享同一片天空。
可當風停了,沙終究會落回原來的位置,細細覆蓋在不同的角落,分界不言而喻。
那時候,我才明白,我只是被風帶進來的那粒沙,短暫飛揚,終究要落在屬於自己的地方。
#2
那年出了一場險些奪命的車禍後,我去了龍山寺,找了一個算命的師傅。
她端看著命盤,看了我一眼,語氣平靜:「還好你總能逢凶化吉。」
「真的嗎?」
她沒有回答,只是遞來一張紙:「你要不要換個名字?」
我低頭看著,紙上寫滿了筆劃精算過的字,每個都看似比我的本名吉利。
「天格不會變,因為它與姓氏相連,是你的先天數理。」她說,「但名字,或許能幫你換一條路走。」
我知道,天格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來自哪裡,與家族的牽連,與出身的宿命。
可我不想只停留在「來自哪裡」,我更在意要往哪裡去。
#3
最後,我選了一個名字。
少淮。
「少」是缺少,是來不及,是停留在某個未完成的時間點上。
但它同時也是輕的,不受束縛的,不被固定的。
「淮」是一條河,是流動,是沒有邊界的。
但它不急著流向終點,甚至可能沒有終點。
這個名字不像某些人的名字那樣,帶著家族的重量,或承載某種期望。
它只是我自己的,是這條路上的某個標記。
但我沒有去改名。
因為改名不會改變什麼,過去仍然是過去,失去的東西也不會因此回來。
可我開始在某些地方用這個名字,在某些時刻以它自稱,像是一種微弱的提醒——提醒自己,不管還缺少什麼,還是要像淮海一樣往前走。
#4
後來,有人問我:「為什麼叫少淮?」
於是我笑了一下,隨口說:「就覺得順口啊。」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這個名字是從缺憾裡生出的,從那些來不及的、沒能留下的、已經失去的,以及決心不再回頭的選擇裡而生的。
這是不是改變,我不知道。
但至少,這次,沒有人能再把我拉回去。
我仍然流動,仍然在路上。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