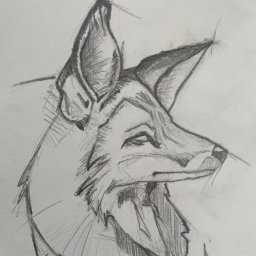昆汀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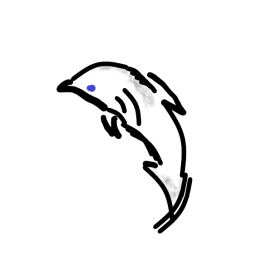
4140
2020-08-31
![]() 歲
歲
0 ,0
大學
個性
平易近人 活潑好動 善解人意 精明能幹 心地善良 搞怪調皮 成熟穩重 性情中人
興趣
閱讀寫作 音樂欣賞 登山健行 唱歌跳舞
電影
劇情片 科幻片 記錄片
音樂
爵士藍調 搖滾、重金屬、流行、實驗音樂
寵物
狗
旅行
喜歡記錄生活,找人互相交流,當然也希望聽聽大家的故事喔!很意外有這麼有趣的地方找筆友,實體或虛擬的文字交流都很歡迎喔~
平時喜歡健身、喜歡音樂、喜歡買書(但速度快於閱讀,所以必須時常趕進度)、喜歡非主流的事物、喜歡出遊、喜歡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