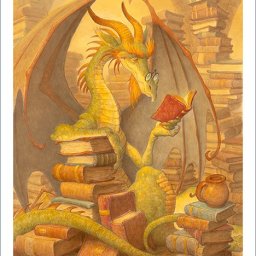For someone...
(純屬虛構)
“人生這盤棋,在將軍了之後也是要照常玩下去的...”(Asimov)
在這世界上有所謂的歐帕茲(OOPART -- Out Of Place ARTifact,即時空不對位人造物體)的存在。這些歐帕兹主要是指一些加工工藝遠超過其周圍文明水準的東西,例如在南美的原始雨林裏被發現的,打磨得完美的幾顆水晶頭骨;又或是本身平平無奇,但是卻在一些不可思議的地點中出現的物體,例如在美國伊利諾伊州所發現的,深深嵌在一塊煤礦中的金項鏈。
我在新幾内亞的高原上倒是有遇見過既已知道出處,甚至認識作者,但也還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歐帕兹。當年我們受了澳洲政府委托,在當地勘察原始部落之中所存在的食人文化與巫毒魔術的傳聞。【譯者按:新幾内亞從1902年起直至1975年一直都是澳大利亞的管轄區。其中的中部高原地帶由於地理環境等因素,直到1960年代都還有存在許多與世隔絕,完全沒與外界交流過的石器時代部落。】我們每到一個新的村莊,除了客套問候以及説明來意,確認對方友善之外,第一個常問的問題便是村中是否有巫師駐在。(對於他們來説,“巫師”這個字可以有很多意思;從貨真價實的巫毒法師起,下至某個特別調皮的小孩子。雖然這樣問往往讓我們浪費不少時間追究一些最終很平凡的東西,但當時我們收到的指示是要讓我們越徹底越好。)
有一次當我們又這麽問時,村裏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忙點頭,說村長的孩子就是巫師,說他會操作一些好厲害的魔法。我們被帶到那孩子所住的屋子前,正好遇到他在門外進行他那所謂的法術。
散落在光禿禿的砂石地上的,是一些造型酷似西洋棋中的棋子的小雕像。男孩(他看起來大約十歲左右,在當地是已經接近成年人的年紀了)在地上畫了一些格子,正在琢磨如何擺放那些雕像。我小心翼翼地在他面前跪坐了下去,用我尚且不太流利的土著語問他他在幹嘛。
男孩說他總是夢見某個很好玩的游戲,可是夢只告訴了他游戲所需的道具,并沒有告訴他怎麽玩。他讓我看了他所雕刻出來的那些棋子:我即刻便能認出兵卒,主教,以及王與后。(在他的夢境裡,騎士是山豬,寶塔成了椰子樹..)他説他似乎感覺到那些小雕像是必須被擺放在某種方形的格子矩陣裏面,但他還沒想好一邊該有多少個格子。
我回頭望向村民,只見他們一臉的恐懼加上敬畏。在新幾内亞,任何擬人擬物的雕像都有可能是巫毒術的媒介體,所以被人們畏懼也是正常的。我想他們沒有很早之前便將這個男孩殺了的主要原因,也只有因爲他正巧是村長的兒子,是有資格與精靈溝通的。
我讓同事把村民帶走,以避免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我接著在地上畫了一個8x8的四方棋盤,然後將他所雕刻的棋子依序排列在兩邊。(他少刻了幾顆兵卒,我以小石子取代)我和他説,游戲的目的是要見到隔壁村的姑娘一面,同時也要確保將自己村害羞的姑娘保護的好好的。(我實在是不忍心以戰事爲題教他下棋。新幾内亞當時成年人的非自然死法裏面還有太多是因爲部落冲突。)我接著向他解釋了各個棋子的走法,吃子的規則,等等。
他聽得出神,似乎是某個想了一輩子的問題終於有了答案一般。他迫不及待地請我和他下了幾盤。我雖然不是下棋高手,但我也察覺得出他似乎是有這方面的天賦:最後幾盤我是在沒有打算讓步的前提下輸給他的。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在完成了當日的作業過後都會抽空到他屋前陪他下棋。迪烈克(我們之中棋藝最好的)對那小子似乎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他下的某些怪陣。我們當時甚至有考慮應不應該把他帶下山,讓他能更好地發揮他的這項神奇天賦,但最後是決定不那麽做。那個年代正是反殖民運動進行的很激烈,所有白人對部落的干涉都被視作褻瀆的時期。再加上,我們那時確實是尚有任務在身,一時間也是身不由己的。
離別的時候,我和他説,這個游戲是神特別讓他看見的,平常沒事的話也就別在其它村民面前擺弄,讓大家操心了。他開心地笑了出來,說謎底已經揭曉了,他還會去擺弄來幹嘛。他還説他現在已經終於可以專心去追真的姑娘了。他當時那放曠又瀟灑的精神,真讓我對那些原始人民的智慧,更加的欽佩了。
圖18,19中的那顆椰子樹和主教,便是當時他贈與我的道別禮。你瞧,這主教是刻的有多酷似我們的主教呀,而他本人卻是連耶穌是誰都沒聽過。我有的時候想,這上蒼開的玩笑中,有些是不是也太過分了一點。明明就知道他這一輩子是不太可能再尋找到第二個對手的,卻還教了他下棋...?可我又想,其實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不也是如此嗎。有些游戲,你琢磨了一輩子也未必看得清楚棋盤或是棋子的樣子,到頭來只是在你的一生中作爲你孤獨時燜燒鬱悶的柴火。如他這般,居然也在第二個奇跡之下,哪怕只是一生一次的巧合之中尋找到了完美的答案與對手的...説不定,該感到悲傷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呢。
——摘自 麥克斯·霍爾頓中校,《新幾内亞回憶錄》
(完)
wZf41UudAbI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