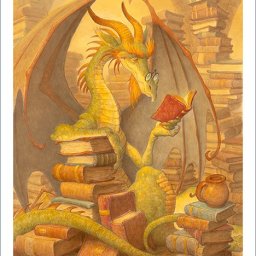“...那個老奶奶呀,聼説家人是越戰時期就移民到美國的。可是你看看她:周圍的環境越是與她所熟悉的不一樣,她便越是把頭拼命地埋進那些已經沒了根的破習俗裏面...”(CPD)
我這一生中殺過許多人,但其中只有一個對我來説是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這個人的命對我來説搞不好比我自己的都還重要。多麽奇怪呀;這種事情裏面總是似乎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帶。
我所言之人,當然就是我的老大,我的賢師;新芝加哥市山元組支部的最後一位當家——森山正弘。他于21XX年4月16日,在我,太田建一的協助之下,死於切腹。
導致那事件的原因,現已不重要了。人從還未成爲人以前就是已經習慣戰事,而森山當時只不過是輸了他職業生涯中的最後一場戰役而已。敵方倒也講道理。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是從日本出來的黑幫,所以念在這份上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遵循傳統的方案:讓森山自殺,然後我們其餘的人解散但從此不相欠。這方案就是俗話説的,那種表面上稱作方案,但實際上是命令的東西。
爲了在當今這個時代飾演這麽一齣傳統味濃的戲,是需要一些事前準備的。森山花了好幾個月,將他身上所有會礙事的各種機關暗器都去除掉:腹部附近的皮下鎧甲,痛覺抑制器,神經自動反射器官..自殺是除非活生生赤裸裸的人,要不然是做不出,做不好的。動物不會自殺。機器人也不會自殺。而人若是體内尚有殘留機械的殘骸,那麽他其實就不算一個真正的人。
安排這事的人也決定,讓作爲他的介錯人,也就是在最後關頭送他一程的我,使用手槍而不是武士刀。將首級砍至只留喉嚨外一層皮的刀術,現已早就失傳了。況且,現存的武士刀每一把都是無價的至寶,是絕對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冒險損壞的。我聼到這消息時暗自喘了一口氣。因爲我知道,這件事要是讓我搞砸了的話,那將比我這一生中所犯的全部過錯加起來都還要再重十倍。
他們也安排好了某個適當的時間與地點。開道場的栗原在聽到我們説明來意以後,傷心欲絕地忍不住開始大罵起來。我們當時除了在悔恨中低著頭承受以外,什麽也説不了。栗原也和森山一樣,被下了一道表面上看起來是拜問的命令。但我想他生氣其實也是有別的原因的。畢竟,他老人家除了在森山的婚禮上哭過一次以外,平常向來都是很沉得住氣的。但他那天終究是哭紅了眼才讓我們帶著回覆離開。我想,那應該是他這生中哭最後一次了吧。
在這裏估且先不談論他與森山的私交,栗原當時面對的問題也確實是很頭痛的。傳統的榻榻米在日本淪陷以後便極難入手,可是用平常學徒們練習用的塑料墊子又好像有點太過分了。栗原最後花了快一星期的時間,將房間内的所有榻榻米都撬起來凃上一層透明的揮發性奈米隔水漆,然後不放心又去買了好幾罐血液中和劑藏在櫥櫃中以備不時之需。森山事前也自願禁食了一星期,說不希望再給人添加不必要的尷尬和麻煩。
不知不覺中,儀式的時辰終於到來。北美洲的所有日系黑幫頭子都到場,排列在房間的一邊。司儀用單調但沉穩的語氣宣告開始,並大致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森山吃下最後一餐,喝了幾杯米酒。一把短刀被擺放在一個精緻的小碟子中遞到他身邊。我走向他身後的某個特定位置。一切都是在完全的沉寂當中,以機械般的精準被執行。
森山向司儀點了點頭。他反握起短刀,一刀刺向自己的腹部,然後先橫後豎直向上拉。當他的動作使得他的内臟開始溢出時,我舉起手對準他的腦後小心翼翼地開了一槍。亞音速的小口徑子彈,算準不會有足夠能量完全貫穿大腦從另一邊射出來的。子彈嵌在他腦中要害的部位,應該是猝死。但他的身體居然也因爲肌肉緊綳的緣故,如當年的弁慶一樣,死後好久都依然保持著挺直的姿勢。
在那之後幾周,街上似乎是異常地安靜。或者應該説,我因爲在家悶了好几個星期,所以對於街上的事情是不聞不問了相應的時間。我其實並沒有必要那麽做。森山的死已經(短時間内)確保了我們的安全。我想,或許我當時只是一個不太擅長面對自己感情的人,被逼得有點不知所措了而已吧。不過我的鬱悶倒也不長久;在那之後我便又重出江湖,又開始與人打打殺殺的了。
有的時候我都會自問,我們究竟是爲了什麽到現在這個地步都還在互相鬥爭,並時不時還舉行類似切腹儀式這種讓外人看了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們可不都是偉大的大和文化遺孤,是都應當好好珍惜自己才對的嗎。像森山那種人,是一旦失去了便永遠取代不了的了。當日我們所坐的榻榻米,也是一損壞便永遠回不來的。日本已經不在,而日本人也終有一天要從這個世上消失,變成只是歷史書與時尚流行中的又一個名字。我一想到當所有的一切都過去之時,我們給地球帶來延續力最長的東西,搞不好會是那些下三流的動畫片的時候,都會覺得不知道是想哭還是想笑。
但是這種在失敗與死亡的面前依然選擇保留尊嚴,貫徹初衷的行爲,才正是代表了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要是我們必須滅去的話,那麽就讓我們挺著胸身爲人而滅去吧。是的,身爲人,那一個唯一能自殺的生物。身爲人,那一個唯一懂過尊嚴真諦的生物。是的,我身爲人,但也即將爲此而逝去。我於是引以感到自豪。
(完)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