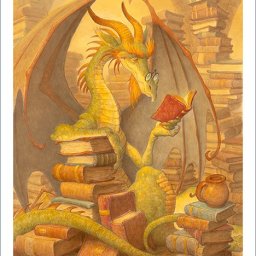在經過了一個星期的勘察和討論後,梅瑞和阿茄回到了特奧辛。小鎮亂得不像樣:破窗子,各種塗在牆上的標語,碎玻璃,破布條和滿地的食物垃圾..仿佛同時經歷過了一場戰爭和一場慶典。鎮上的父老們在會議堂接見梅瑞,和他說他的計劃被通過了。他們給了他一箱裝著五百兩銀子的木箱,並說整個社區的資源從此都供他使喚。他們還說已經安排好了一輛馬車,讓他把銀子帶回離間斯堡,並問在他回來之前是否有任何他們可以先做的事。
梅瑞拿起了一條銀子。在金屬的冰冷反光裡他看到了自己此行的所求之物:兩三年的自由時間,能夠讓他隨心所欲而不用去乞討畫費。但現在一切都顯得如此渾濁。他瞄了一下阿茄;她站在窗邊,並沒有要插手的意思。他把銀條放回箱子,蓋上了蓋。
“你們派別人去吧,”他說。然後就在父老們都摸不著頭腦的時候,他開始大笑了起來。
他笑啊笑,笑著自己如何那麼輕易地就把夢想和理想都給拋棄了。
* * * * *
“我那時來到山谷已經十一年,而畫則已開始了十二年。我對那其間發生的變化感到膽寒。許多的山頭都被砍得光禿禿的,而野生動植物也少了很多。當然,變得最多的是克理奧。鷹架從他的背上垂掛著,吊著工匠在它的側面又塗又磨的。通往它頭上的木塔無時無刻都擠滿了勞動的人,上面的大火爐在夜裡對天空噴著火,好像一座蓋在天空中的煉鋼城。在它的腳下一個簡陋的棚戶區建立了起來,裡面住滿了妓女,工人,賭徒,各樣的混混,和軍人;計劃所需的巨大開銷促使特奧辛的父老們組織了一個民兵團去洗劫甚至佔領周圍的地區。屠宰廠附近圍著一群群在等著被煉成油和顏料的可憐動物。街上到處都是載著礦物石和蔬菜的馬車。我自己當時就運來了一車用來製造玫瑰色的茜草根。
想和卡達內見個面並不容易。雖然他從不參與實際的作畫,但是他總是在辦公室裡忙著接見工程師或工匠,或是忙著安排某些運輸上的細節。當我終於見到他時,我發覺他改變得和克理奧一樣劇烈。他的頭髮已經發白,臉上也都是皺紋。他對於我想買那幅畫,也就是在克理奧死後把構成畫的鱗片都買下來一事感到很好笑,而我覺得他一開始根本就沒把我的話當真。但他的助手阿茄,那個總是伴在他左右的女人,幫我買了個人情。她和他說了我是個負責任的商人,還說我已經把骨頭,牙齒,甚至是它肚皮下的土都買下來了(我後來把那些土當成某種秘藥出售)。
“嗯,”卡達內說,“我想到時候總得要有個人擁有它們的吧。”
他帶我走出去看那幅畫。
“你會把它們留在一起保存嗎?”他問。
我說,“是的。”
“那如果你願意在紙上承諾那件事,那它們就都是你的了。”
我當初以為會為了價格討價還價很久,所以他的坦率其實還蠻令我意外的。但是讓我更感到意外的是卡達內接下來那句話。
“你覺得這畫畫得好嗎?”他問道。
卡達內並不認為那幅畫是他自己的創作。他覺得他只是在為克理奧側面的形狀上色。而每當一層油漆被塗上後,他又會覺得有新的形狀產生,從而不斷地把顏色改了又改。他把自己看成更像一個工匠而非一個創作藝術家。但就他所問的那個問題來說,倒是真的有很多人開始從世界上各個地方來觀看那幅畫。有人說能從中看到未來的啟示;有些人聲稱經歷過出神的狀況;而更有些人——主要是一些畫家——嘗試在畫布上描繪原作,似乎想藉著模仿這一作品而樹立自己的名聲。
那幅畫本身是抽象的,它基本上就只是一片塗在大龍側面的金色油漆。但隱藏在那漆光的表面下的是無數種彩虹般的顏色,並會隨著太陽的移動變成無數種不同的形狀和圖案。我不會在這裡試圖說明那些圖案的種類,因為它們似乎是無限的。但是我敢說,當我與卡達內見面的那天早上,我,一個自認務實至極,腦子裡沒有半點藝術氣息的人——感受到自己似乎被畫吸了進去,穿越過由光組成的形狀和彩虹色的花紋,看到了像雲一般自由變動的火球,螺旋,和風火輪……”
——摘自『克理奧生意談』,亨利・西奇著
(待續)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