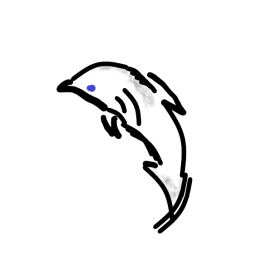那天,我一如既往地去了高雄的音樂祭,看著一如既往地衝撞跟歡鬧,都是一如既往地。
而一如既往地,我早已忘記那年的感受,無論我看多少次音樂祭都一樣。
真的,這已經是我今年第四次去音樂祭,依然如此。
海豚刑警還是那麼的熱鬧,音量總是那麼大,台下的觀眾還是好熱情,
嘻笑、叫鬧與混雜著啤酒的臭香麥味散佈在炎熱的七月中,
如同蒲公英種子隨風飄散,彷彿也把這些熱忱、單純靈魂的氣味散佈下去,
可是怎麼著,心中卻沒有什麼波瀾,
又或者說,是不是自己築起一片片灰黑色的消坡塊,
避免潮起潮落,讓浪花又侵蝕了那片心土呢?
不重要,確實一點也不重要。
正當我以為我又要掉落那個深淵時,一個輕巧的聲音拉了我一把。
「嘿,一個人看音樂祭喔?」
我轉頭過去看,一個染著綠色短髮的女孩子看著我,
傳來的除了那杯早已退冰的威士忌可樂味道,還有衝撞痕跡的體味,
雖然有點重,但並不討厭,或是說,有一點點討喜,
她帶著點笑意,用拿著酒的右手頂了我一下,點點頭對我說。
「對啊,感覺妳也是。」
我轉頭過去,對著她這麼說著。
她又是那張半笑不笑,有些神秘、有些促狹地眼神看著我,
手指著我T-Shirt上被單眼相機遮擋著的圖案,說:
「這是velvet underground的衣服對吧?挺有品味的啊!」
我低著頭,看著衣服上圖案,說:
「謝謝。對,這是VU的衣服,2010年在紐約剛好朝聖,看到他們的表演,剛好買的。」
「那時候Lou Reed好老好老,臉上滿是滄桑,我就在想,原來人可以長這麼老。」
「他好清瘦,聲音好輕,但還是好有活力的哪種感覺欸。」
「當時我還以為他就會這樣一路搖下去,搖到一百多歲之後。」
「不過誰知道,過沒幾年他就去世了,這大概就是人生無常的意義吧。」
她看似在思考什麼樣子,側著頭聽著我說話,
好像有深遠的看著我,淡淡的說:
「對啊,人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什麼意外出現,所以才要把握當下吧!」
語畢,她忽然爆出一陣大笑,然後哈哈笑了一段時候,
用沒有酒的手拍打著我肩膀,說:
「欸!?我們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老人發言啊哈哈哈哈哈!」
「拜託,來音樂祭就是要開心,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拉!」
「不要看起來一臉苦瓜樣了拉,欸!要不要喝酒?我請你哈哈哈哈,不用錢拉!」
她後來邊走邊告訴我,她也是一個人來音樂祭看表演的,
沒事的時候,就會觀察四周的人,看形形色色的人群長什麼樣子,
剛好,她發現有個男生每次都穿一件外國的團T、一件黑色牛仔褲跟黑色Converse,
靜靜地站在某個地方,然後靜靜的看著表演,
偶爾呢,會用脖子上掛著Ricoh的小相機,捕捉演出的各種風景。
「當時我就猜,你滿特別的,不像其他人總是喜歡戴好大一台單眼裝逼。」
「反而看你這樣低調的感覺特別有一種酷氛圍,你懂吧?」
她是這樣說的,不過我沒跟她說的是,
當初買Ricoh就是為了要裝逼把妹用的,因為想假裝森山大道街拍,
加上平常好像很少看過有人買這個牌子,覺得很特別才買的。
「然後啊,我連續三個音樂祭都看到你出現,說真的,你很閒喔?」
「我就在想,要是第四個音樂祭再看到你出現,我一定要去搭訕你!」
「啊,就這樣想著想著,你就出現在我右前方哈哈哈哈。」
「你知道雷達鎖定吧?就像捍衛戰士的飛彈一樣喔,我一鎖定就衝過去」
「結果就找到你拉哈哈哈哈,我想這就是緣分吧!」
我在想,這不就是妥妥的跟蹤狂嗎?是嗎?我也不知道。
但因為覺得有意思,所以就不覺得有什麼了。
她拉著我跑去販賣部,問我想要什麼,我說可樂娜,她立刻就答應。
她笑嘻嘻的看著我,說有酒的音樂祭才是真正的音樂祭喔。
我只是看著她耳垂白銀的三角型耳環晃呀晃的,配著那輕響的嗓音,滿配合的。
身型瘦小的她,穿著牛仔短褲,我想,音樂祭應該很多人會想搭訕她吧。
啊,不重要吧,我想,什麼也不重要。
我和她走去主舞台晃晃,樂團主唱正在激情狂吼著,
配合著節奏極快的鼓聲,台下的觀眾瘋狂地四處叫喊著,
而她,配合著旋律應聲吆喝著,但也配合著我,站在一旁看著。
「欸!!為什麼你喝了酒,還是一臉苦瓜樣呀?」
她邊看著表演,用著有些喊啞的嗓子對我這樣說。
「沒有拉,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好像開心不太起來。」
我呆立在喧囂的草皮上,如此這般的回著。
她聽完,難得收斂起笑臉,轉動著靈動的眼神看著我,
歪著頭,思忖半宿,對著我說:
「你是不是,也剛失去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我跟你說,我很敏感的喔,眼睛可以看透所有。」
「你眼睛深處感覺覆蓋了點說不清楚是什麼東西的遮蔽物。」
「一般人可是不會有這種東西的,一定是刻意被放上去的。」
「那層遮蔽物,是為了避免被再次傷害,才深深纏上去的喔。」
「別看我這樣,我職業是靈媒喔,可以一眼看透本質,厲害吧!」
她後來跟我說,那一切都是瞎掰的,
可是那個瞬間,我彷彿被重擊了一下,
一瞬間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眼淚一下子就潰堤了,
雖然很丟臉,當著3000多人的大場子哭泣,但確實忍不住。
她看我哭了出來,先是一愣,
接著,溫柔地把我懷抱著,即便她只能垂靠在我胸前,
雖然感受到眾人的眼光投射,卻毫不在乎的擁抱著我。
她輕輕的抱著我,說:
「沒事喔,我在,沒事。」
我用右手擦抹著眼淚,回說:
「謝謝,真的謝謝妳。」
音樂祭還是那樣一般,一如既往地演出,地球還是一如既往的自轉,
而伴隨著各種人聲及樂器聲響過後,確實有什麼事情不太一樣的。
後來她說,她也是因為失戀才去音樂祭,想沖淡點什麼,
她感覺我好像也是,憑藉一股動物的直覺靠近,
其實搭訕前很焦慮,焦慮對方會不會覺得是怪人,
誰知道對方竟然就答應一起喝酒、一起看表演。
看到我哭了,心裡很慌,
但她想想,既然彼此都是汪洋中那一條小船,
雖然不能確定對方心思,但當下她認為還是互相扶持吧,
被罵就被罵吧,可能被當騷擾就當騷擾吧,就抱了我。
雖然我也說不出這是什麼感覺,不過卻覺得很穩,找到點定錨。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