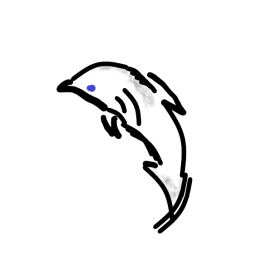週六的夜裡,我依然無所事事的窩在租書店,時鐘上指著11點23分,距離關店已經過了1小時又23分鐘,但我還是不知道要幹什麼。順手把早已翻爛的爆漫王第3集丟到旁邊,嘴裡嘟囔著說:「媽的,我要有真城的實力,早就娶到小祚了。」
小祚是我和老B所組的樂團主唱,同時也是一個奇妙的存在,在某次白痴的告白中,她笑嘻嘻的答應了我的追求。
那晚,早就忘記是幾月幾日了,我們在美提的河濱水岸看著滿月的月色,皎潔的白光映射於波光粼粼的基隆河。我和她坐在掉漆的石椅上,維持戀人未滿的距離,那天,我們下課去吃了貴得要死的黑輪店,平凡無奇的關東煮居然貴得驚人,硬是在隨處可見的無聊食材上展現了奇詭特色,我以前常笑說這間是盤子光顧的店,想不到哪天因為寒流來襲,冷風一陣又一陣的颳在我們身上,小祚莫名提議說想去吃個關東煮,喝點火鍋料煮出來的柴魚片湯,於是乎,我成為了那個盤子。吃完之後,小祚說想去河濱走走,我們拿出隨身攜帶的學生證,刷了Ubike,騎著黃色的菜籃腳踏車去美提附近,停妥後,我們步行走了進去。
小祚穿著米白色的帽T和牛仔短褲,手機顯示著12度氣溫,必須說,雖然她很可愛,但穿衣邏輯比咄咄逼人的奧客還差勁。我問她「妳不冷啊?」,她回我「我是火焰超人冷什麼?」,果然很可愛。其實我也沒什麼資格笑她,在寒冷的夜裡,只穿著一件繡滿龐克布章薄外套,那件外套還是我在yahoo拍賣買的便宜貨,因為我想說,反正便宜的縫起來也不心疼。
小祚指著上面的布章說:「S....O...B!?我還以為是S.O.D.欸!」
我笑著說:「哇靠,看來妳也是略懂略懂欸!」
她笑著回:「還不是被你和老B害的,整天說一堆有的沒的哈哈哈哈」
我忽然站了起身,擺出一個主唱抓著麥克風架的姿勢,說:「沒有錯拉,但這不一樣喔,S.O.B.可是超屌的老牌龐克碾核樂團喔!啊啊啊啊啊!!!!」
她呆呆的望著我,秋波中看不出任何訊息,只知道她嘴角微微上翹,撇了一句:「你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我還正幻想著自己是主唱,邊甩頭邊說:「怪啥,妳在笑我喔!?」
她說:「沒啊,我怎麼會笑你,我只是覺得你很奇怪,奇怪的很好笑。」
當時我右手伸出拳頭對天,接著彈出食指與小拇指,像是想要昭告天下般的說:「沒錯!老子就是這個世界的奇怪惡魔王,其他惡魔聽我號令,皆陣列在前!!」
小祚眼見我那個蠢樣,更是笑得合不攏嘴,拍著雙手,然後左手扶著額頭,不斷地抖動肩膀。在微弱的月光下,雖然看不太清楚小祚得臉,卻又照得有些清楚,雙眼皮、白皮膚、黑頭髮,烏溜溜的短髮有些反光,在風吹的狀況張狂四散,她捂著嘴笑得燦爛,眼睛瞇成一個上弦月的樣子,我真實的感受到她好真誠,真誠到我彷彿可以從她的雙瞳看見她整個人的靈魂,細細的頑皮笑聲在我耳邊轉動著,我發現,她舉手投足都好可愛,任何一個動作都好可愛,就像她每次練團時,像一個中世紀、穿著白色衣裳的女精靈在歌唱般,纖纖身形手舞足蹈,她總是那樣真誠地享受在每一個時刻,我覺得她好迷人、好迷人,她總是那麼那麼的迷人,勾住我的雙眼和心思,我想,那是一種可以名之為「戀愛」的感覺。
我決定,要告白。
當時我不知道哪裡折了一根雜草,小祚問我要幹嘛,我說不告訴妳。我手抓著綠色的長條葉子,把它捲成一個圓形,然後在相接處打了個結。沒錯,我打算做一個戒指。拿著剛做好的「雜草戒指」,相當正式又開玩笑的形式準備告白,天曉得,如果不是用這樣的形式,或許這一輩子都說不出告白的詞語。可是,硬體準備不是大問題,問題是心裡根本沒想到要講些什麼,但為了讓自己可以真正地說出告白的話,還是硬著頭皮說出那句:「小祚,我有話要對妳說,很重要很重要的話。」
小祚被我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傻住,她嘴角褪去了笑意,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我,說:「發神經喔?什麼事?」
由於,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說出這句話,加上過去又沒有告白的經驗,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要說什麼。只能支支捂捂的說:「誒....就是....誒....啊」。天阿,沒想到告白在漫畫上看起來那麼簡單,做起來這麼困難,心臟一直跳一直跳的,跳得彷彿要從食道跳出來,然後往基隆河一躍而下游泳去,當時臉很熱、耳朵很紅,說了些許廢話,就是說不出想說的話。
小祚看著我不安侷促的樣子,倒也不逼人,反而把頭擺過去,靜靜的看著河岸上的月色說:「不急,等你準備好了再跟我說吧。」
看著她溫柔的側臉,體貼的樣貌,忽然,我從原本的緊張,居然漸漸轉變成一種害怕的感覺。這個道理是這樣,一直以來,我總是被小祚的可愛所吸引,覺得好喜歡這樣可愛的她,一舉一動都是如此,於是有一種很激烈的戀愛感覺,感覺想要好好的跟她在一起,想要一起過上一輩子生活。可是,我就只想到這邊而已,完全沒有想過說,自己是不是真正的配她,她不僅是那麼可愛、那麼有才華,可是,她也是那麼的溫柔與體貼,而我,總是做事衝動,用一種近乎直覺的方式在過每一天,要說我只是一隻會使用大腦的狗都沒問題,玩團玩的不上不下,住在老闆借租的破舊漫畫店樓上,每個月打工才不過2萬5而已,這樣的我,會不會根本配不上她,又或者說,她其實根本就不會喜歡這樣的我,不會喜歡跟這樣的我生活呢?一想到這,就覺得好害怕,害怕這話一說出口就會打破所有的平衡,一說出口就做不回朋友,永遠止步於熟悉的陌生人,然後逐漸消失在彼此的生命中。
不,我才不要這樣,我覺得只要能夠這樣靜靜看著她很可愛就好,說不說的,就這樣吧,就算沒有在一起也沒關係吧,但我真的很想要就這樣一直看著她側臉到最後。
於是乎,做完決定的我,將一直在手上把玩的雜草戒指丟到一邊,直勾勾的看著被風吹動的河面,背側著身,緩緩地吐出一句:「算了,不說好了。」此時,從眼角餘光看見小祚像是被電到一樣,整個人從遠本駝背的坐姿挺立了起來,然後瞪大了她的雙眼,用一種不可置信的表情看著我,然後聲音高了不知道幾度,細聲說:「什麼拉?!怎麼可以不說啊?!」
被她反應嚇到的我,不知所措的說:「啊...???就先不說啊....安怎!?」她聽完我說,倒抽了好大一口氣,那個呼吸聲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聲音持續了至少有三秒。接著,她忽然垂著頭,然後繼續看著河岸不發一語,當下,我只覺得,不知道要說什麼的時候,河岸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當時,我們都好安靜,風聲遠遠超過了我們的呼吸聲,在滿月的見證下我們靜謐了超過一分鐘,然後小祚才打破了沈默。
「好拉,你不說就算了。」我記得她當時是這樣說的。雖然我不是那種很懂得察言觀色的人,卻可以感受到她語句帶有些無奈,於是問了句:「幹嘛拉?」
她轉頭盯著我看了許久,又轉頭回去看河岸,帽t的連身帽跟著身軀扭動著。接著,正當我打算再問一次幹嘛的時候,她默默吐了一句:「你是不是想要告白啊?」
那個瞬間,原先的緊張感又跑了回來,腎上腺素激增著,血液流動又變得快速,平靜得呼吸忽然又急促了起來,心臟又開始撲通撲通的跳,果然,五月天的阿信並沒有騙人,一顆心,真的會撲通撲通的狂跳,閉鎖的胸腔感受的那彈跳的觸感,就像有一個藏在裡頭的拳擊手不斷對著皮膚打出一記又一記的重拳,轟的我連耳朵都聽到那個聲音。「啊奇怪??她怎麼會發現???」是當時迴盪在腦海中的一句話,冷汗直流的我卻不敢吐出什麼,只是任由不受控制的身軀顫抖著。小祚看著我不說任何一句話,就再次重述了那句震耳欲聾的問句:「欸,所以,你是不是想要告白啊?」
我近乎不可思議的看著眼前這個女人,她到底為什麼會如此輕描淡寫地說出這樣可怕的話語,難道她都不怕說對方其實一點也不喜歡她嗎?一直到很後來才曉得,小祚看似柔弱,但對於感情觀卻十分堅定,她認為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要是對方真的沒有要告白,那她也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就是猜錯了而已。可是,我並不知道這樣的心聲,只是覺得面對這樣直面的話語竟然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只能默默點頭,顫顫巍巍地說:「欸......對餒....」。
小祚看著我,嘴角像是似笑非笑的,接著說:「白痴,那就告白啊。」
被她這麼一說,我忽然覺得,對方都這麼大方了,自己也沒什麼好扭捏的,於是,我說了句「好喔」,轉過身,說:「那你要等我一下」。小祚點了點頭,表示沒問題,而我則是探頭又去找了合適的雜草。摸著黑,被我看到了一條長約20公分長的酢漿草,伸出手拔了起來,用著同樣方式做成了一個雜草戒指。必須說,當時的我還是有點堅持的,哪怕是蠢到瘋頭,但有些儀式感的東西還是要做的。小祚發現我好像在做戒指,忽然爆出一陣笑聲,然後用手捂著嘴巴,像是知道怕我會覺得丟臉而忍住的笑意,只是雙肩抖動的幅度還是掩飾不住她的歡樂。
「欸,妳真的是很靠北欸,笑屁喔?」我對著小祚這樣說。
「沒有拉!你不要誤會,我只是覺得你很可愛而已」小祚略帶微笑的說著。「所以,你那個是戒指嗎?」
被戳破的我,這時也覺得好像沒什麼好在乎的了,於是不甘示弱地說:「對拉!怎麼樣喔?」
小祚笑盈盈的看著我,然後說:「好喔,那你要開始你的『求婚』了嗎?」
「白痴喔!」我大聲回著。「結你媽婚,我們都還沒在一起就要求婚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喔好喔」小祚被我這句話搞到笑出來,然後說:「所以,你想要幹嘛?」
我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說:「告白拉!」。小祚聽完我這句話,收起了笑臉,靜靜的看著我,等待我接下來要說的話。在滿月的照耀下,我單膝下跪,這一跪,小祚挑了挑眉說:「你不是說不要求婚嗎?」。而我,只是回了句:「你不要管。」「好拉,我不要管」小祚如此這般的回我。拿著那個雜草戒指,高舉在空中,裝腔作勢的用演講的那種噁心做作語調說:「祚小姐,請問您,是否願意與拓先生我,交往呢?」
小祚看著我,像是本來要說話,結果還是被這個奇怪的場面逗樂,爆出一個好大的笑聲,而我也因為這舉動實在太過愚蠢,也笑得樂不可支。
「幹你真的是智障欸哈哈哈,可以不要把這麼浪漫的場景弄那麼搞笑好嗎?」小祚笑得喘不過氣,這樣對著我說。
「哈哈哈,靠北喔,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交往拉哈哈哈!」我笑著回。
「好拉好拉,可以拉,我答應跟你交往好不好,那要交換戒指嗎?」小祚邊笑邊這樣說著,我說「好」。於是,我們這對新人,摸黑再度去找了另一條合適酢漿草,做了另外一支戒指,戴到無名指上,然後用samsong手機邊笑邊拍了一張照片紀念,雖然,白光照耀的月亮看不清楚它的表情,不過我想,它應該也在笑吧,笑我這個白癡又愚蠢的人。
交換完「戒指」,形式上來說,我們算是確認了關係,於是我大膽的牽起了小祚的手,而她也大方的緊握著我,我們又是看著河岸,一句話不說。
這一次,打破沉默的是我,我說:「欸,不過小祚,先不說妳是怎麼猜到我要告白,妳為什麼會想跟我在一起啊?」
小祚還是看著河面,說:「因為我本來就喜歡你啊。」
我說:「喜歡我?也太奇怪了吧,我覺得我自己根本就像是一隻老鼠一樣,根本沒啥值得喜歡的。」
她歪著頭,疑惑的說:「啊?老鼠?」
「對啊,老鼠,像是那種城市中隨處可見,人人喊打的髒臭老鼠,活在底層的社會。」我雖然是對著河面,但卻是對小祚說這段話。「每天高不成低不就,永遠都在為了生活在拼命的感覺,像我,住在老闆租給我的破舊地方,也好像沒什麼遠大夢想,就窩在那個小小小的地方。」
她沉靜了半晌,回說:「那你要這樣說,我其實也是老鼠啊,我也沒有什麼成就,每天都在超商打工,和室友擠在小小的套房,為了拿到獎學金不得不做一堆報告和作業。不過,至少老鼠還有一些自由吧,反正沒有人會管牠們,到處跑就好。」然後她側著身,用正臉看著我,平淡的說:「嚴格來說,我們就是兩隻老鼠吧。」
那句話直至此時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兩隻老鼠,那象徵著底層、不堪卻又自由的角色。雖然,小祚就像爆漫王的亞豆一樣,成績優秀、努力打拼和可愛親人,根本一點也不像老鼠,不過她還是願意屈就於我,同樣把自己擺在老鼠的角色上。此時,好友老B提著從三和夜市買回來的三兩三滷味跟超商買了一手金牌回來,對著我說:「欸,餵食時間到,他媽不要像個死人一樣,起來了。」
「他媽的,我們才是兩隻老鼠吧?」
「殺小?你他媽是不是抽菸抽到腦子壞掉啊?」
「靠北喔,沒事,來吃東西。」
破舊的漫畫出租店透著昏暗的日光燈燈光,充滿污漬的白桌上清出空間,在煙灰缸旁放著塑膠袋,裏頭裝著豆腐、豬肝等滷味,我們開著黃色鋁罐的金牌,用一點也不環保的竹筷子夾著食物吃,聊一些日常又無趣的事情,日復一日的,吃著、聊著、生活著。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