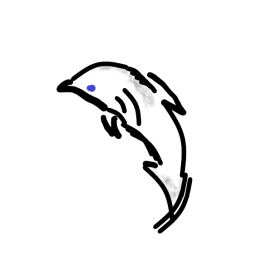日頭與地平隨著軌道偏移越發的拉近,橘黃鮮豔的烈陽把無趣的小日子給曬熱,如那群窩在一堆準備脫穀的白米,隨著水分的抽乾而褪去褐色的戰盔,將晶瑩剔透的美驅橢幹展露無遺。米白色的床單平鋪於彈軟的眠床之上,為原初坦胸漏乳的它綴來一薄紗,不讓俗世的塵埃髒污了純潔的它。老媽在幾個月前,操著口流利的台語跟我說:「那眠床舊漚舊臭啊,躺在頂頭攏要崩去啊,緊換換欸拉。」,她在一間床墊專賣店試躺了好幾回,才決定讓那副陪了我十幾年的乳膠床墊跟著樓下神龕的關羽持書神像一併請出了家門,迎來了一尊觀音慈眉像與一尊獨立筒的高價床墊,老媽說這床很貴,要好好珍惜,而我還來不及為初始離去的舊識友床悲戚默哀,就深深的被那深深吸引住身軀的新床友深深吸引,在那個當下我就知道我的未來要好好珍惜它,好好地將自己的未來托付給它。
晴空萬里,風光明媚,桔紅的夕光尖銳粗暴的折射進房間,我那如胡亂塗鴉的肌體如藝術品般照耀在櫥窗邊,如美術館內館藏的展示品般,毫無感情的托在被褥旁。新刺好「蒼蠅王」刺青仍隱隱作痛,幾絲癢意慢慢傳導進腦中,透明的風扇仍韻律的旋轉著,讓氣流輕拂著傷口,皮膚滲出幾點血滴正哀嚎著疼,蒼蠅王口吐的縷縷黑煙也從皮膚滲入骨肉,無以名狀的恐懼緩燥而起,從我後腦勺走到前額處,再走到眉宇之間,再走到鼻翼雙邊,再走往唇齒相連之處,接著從頸部竄入食道內,如高速鐵路般的狂飆極撞在胸膛。蒼蠅王展翅高飛,薄翼翅鞘風馳電掣的互擊,房間內瞬間充滿著壓抑而嘈雜刺耳的巨響,吐著黏稠嗆鼻腥臭唾沫的口器呼著難忍氣息,密集格狀的複眼接縫處盡是令人作嘔的粗黑纖毛,鮮豔青綠的六角角膜使我毛骨悚然,而無紋光亮的晶狀體所映射出的是我瘦骨嶙峋、面如白蠟的雙頰,與那了無生意的瞳孔。
忽然,蒼蠅王不知為何侷促不安的飛去,同一時間木門吱吜的一聲被扭開了,我往旁邊一看,原來是老媽走了進來。她看著滿頭大汗的我,像是有些責備的叨叨絮絮說:「阿你怎麼長這麼大了還不知道熱要開冷氣啊?」。接著走到那台新裝的分離式冷氣機下,抄起白色塑膠製的空調遙控器按了幾下,只聽緊連天花板的長型機械巨獸張開了口,如那遠居他處的青女,捲起冰天雪地的霜息寒意來到凡間。開完冷氣之後,老媽稍微整理一下我昨晚喝剩的咖啡罐子,然後對著我說:「樓下爸爸有買三寶飯,還煮了一鍋你喜歡的鱸魚湯,餓了記得下去吃。啊吃完之後要記得吃藥喔。」。語畢,在她強烈的要求之下強制清空了桌面的垃圾與房間內的垃圾桶。
在我十七歲時,因為一次印象模糊的事件,爸媽帶我去各處求醫、諮商,長時間的服藥後也我發現自己的身體變得跟十七歲以前有點不太一樣。我曾經以為在銳舞派對上遇到的麥角酸二乙醯胺可以帶我脫離痛苦、進入禪定涅槃的境界,不過當強烈的痙攣與眩暈嘔吐出現以後,發現不一樣的只有對於世界的感官感受而已,時間的意像與空間的異象經常讓自己處於一個透明無息的詭譎處,而一切的一切都顯得毫無意義。老媽是一名診所的藥劑師,她總是能如超人般帶著我在刀片刮除幾片皮膚後趕往診所找護理師阿青阿姨清創、注射消炎藥。阿青阿姨每次都會氣急敗壞的說:「哎呦威啊!!阿你怎麼又來了????」然後大力的用鑷子夾著沾滿食鹽水的棉球刷起傷口,邊跟我老媽說接下來要怎麼做護理。
我老媽每次看到清創的畫面都會哭,幾乎沒有一次是不哭的,然而我看到她哭我自己也會哭,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哭,我只是單純覺得我好想要哭,覺得她好像把她的眼球移植到我的眼球之上,接著如雙胞胎的靈異共感般同時淚眼潸潸。不過從我有印象以來,她似乎沒有真正怪罪過我一次,只是一再的訴說:「記得吃飽飯要去吃藥喔,不要亂忘記喔!」
斜倒在床墊的軀體懶洋洋的臥在一旁,右手畢露的青筋紋理暗示著某種生命的存在。黑色的衣物殘存昨夜的香水味,是一位在音樂祭認識的女孩,染著標誌性的楓紅色短髮,和隨著撞擊節奏發出的高亢淫蕩的呻吟聲響,完事之後她赤裸的倒在一旁睡去,頭枕著我腰際,滴圓兩瓣的乳房依偎在腿側,而我拾起波特萊爾的詩集「惡之華」,信手翻至「貝德麗采」(La Beatrice)篇,詩句寫著:「我心中目光蓋世無雙的女王,她也一起嘲笑我陰鬱的痛苦,有時還給它們些淫穢的愛撫」。看著穠麗豔華的文藻,竟憶起了剛剛那欲仙欲死的激烈性愛,下體的溫熱濕暖觸感及唇舌舔拭的激烈,原先垂痿的叢根又逐漸聳立而起,內心忽然有著止不住的蕩漾悸動,腦中無法克制的浮現各種奇異遐想,對於奇詭刺激的性愛方式有了更多畫面,激情、暴力、強烈的情緒在體內不住的衝擊,彷彿當下的自己竟已不再是原先的自己,然而忽然陰莖彷彿被一股溫軟細嫩的感覺包覆,往下一望,那裸著兩乳的紅髮女孩笑嘻嘻的看了我一眼,櫻桃小嘴含住了硬玉,接著略微把頭往上一台,將根處往外一吐,最後俏皮的伸出舌頭舔向根膚,說著:「你好壞喔,你又想要了嗎?怎麼忽然變這麼硬了?」。然後起身,雙唇吻了一口,眼神迷離朦朧的看著我,嬌驅前傾,刻意地用乳頭輕抵著我的胸,兩頰暈如晚霞般,柔聲輕道:「我還要。」
而我雙手撐起,回顧昨夜種種,僅能記起情節,卻毫無興奮之情,只感覺垂頭喪氣、悒悒不樂。如遠方望見盛開毛茛一片,以為尋覓到群花綻放的天堂淨土,卻被莖部毒素染的嘔吐、甚或器官衰竭而敗,以為自己找到一種快樂的方式,不過最後的最後依然是象徵著死亡。走向床頭音響,播放起紅粉鍊人的新專輯「怎麼老是你How old Are You」,實驗性質極為強烈的即興聲響是唯一能讓恐慌的自己放鬆的方式,雖然諮商的姊姊總是告訴我可以試著去找其他舒壓的方法,可惜到目前為止似乎仍止步於緣木求魚。
花了點時間,聽了兩首瘋狂的歌讓緊繃的情緒放下,一首是「羊瑜伽具」、一首是「me n'u vs. u n 'em」,真不愧是自由爵士樂手謝明諺跟電子實驗家鄭各均合力製作的音樂,狂氣的薩克斯風與無調性的鋼琴噪音交互影響下讓原先浮動的心又沈潛於海底。安心之後,生理機能逐漸恢復知覺,漸感到飢腸轆轆,於是下樓去吃老爸準備的午餐。老爸邊看著MOD頻道的「澳洲頂級廚師第十四季」,邊對我說:「哎呦,起床了喔?吃飯喔!有魚湯、有便當,看你要吃什麼,阿晚點我要去菜市場買排骨煮晚餐,你要不要一起去,順便去買你喜歡的壽司」。老爸知道我鍾情於台式壽司,每每到附近的北平路黃昏市場都會記得多帶一份回來。我說好,剛好等等沒事,就想著可以一起去。
身爲一名蓄著長髮又渾身刺青的男子,走進黃昏市場不知為何總有一種疏離感,人們懷疑懼怕的眼神似乎認為我是什麼特立獨行的瘋子,尤其混亂的圖案間可能夾雜數道傷疤,幾名上街買菜的民眾往往會刻意遠離我,或是不敢與我對眼等等。不過能夠把我從另一個世界拉回現實的人是老爸,他總是用極為正常的方式跟我、跟他人互動,並且熱情的跟我介紹攤位的鵝肝便宜又好吃,要不要切個幾顆回家嚐嚐,我說好,於是老爸就上前搭話去。攤位的叔叔瞧了我爸一眼,又瞧了我一眼,表情似乎有些僵硬的說:「哎呦!連仔喔,阿你擱來買物件喔?啊這誰?你後生喔?」,老爸笑著回說:「嘿啊,有緣投某?」,攤位叔叔則說:「有拉有拉」。叔叔從鵝油高湯裡撈出幾塊象牙色的鵝肝出來,俐落的用菜刀切了幾份裝成一袋,滿滿當當只要50元,我主動掏錢要付,老爸沒有阻擋,只是笑著說:「好拉好拉給你付」。然後攤位叔叔從我手中接過錢,而我接過香氣四溢的鵝肝,這才看到叔叔面色稍微和緩,接著說:「連仔,你後生很友孝喔」,老爸則是拍拍我的肩膀,說著:「嘿啊,很乖拉!」。
逛完菜市場,買完排骨跟四物的中藥方回家。老爸說,知道我喜歡吃四物湯,每次都會先拿米酒泡一下當歸來行藥,讓湯頭可以更濃厚一些,最後點些紹興酒讓湯頭喝起來不要太銳利太苦了,這樣就剛好符合我的口味。我幫忙切點排骨、洗洗刀具,老爸則是燉湯煮晚餐,等老媽下班回家吃飯,最後晚餐我們一家三人配著可口的鵝肝、中藥排骨湯跟炒麵相當日常的結束。回到房間後,繼續放著紅粉鍊人的新專輯「怎麼老是你How old Are You」,歌曲剛好走到那首「媽禱ㄕㄨㄞˊ」。那首其實不是歌,是紅粉鍊人錄下跟媽媽對話的日常內容,內容是媽媽為紅粉鍊人禱告,還有幾段溫情的互動,透過床頭音響都可以感受到那股瀰漫而出溫馨,不知為何,兩眼忽然又如轉開水龍頭的狀況,淚水梨花帶雨般的落下,又是那無法克制的狀況。唯一能有意識控制的,是走出房門,看著在客廳看Youtube的老爸老媽,他們看到我兩眼汪汪神色有緊張,趕緊問我發生什麼事情,而我只是抱著他們,不住的說:「爸爸媽媽,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老爸聽我說著這麼一段話,倒也沒說什麼,只是又是拍拍我肩膀,眼匡似乎也有點紅了些,說:「謝什麼拉,不用謝不用謝」,老媽同步說著:「對啊,不用跟爸爸媽媽說謝謝拉,只要你有健健康康就好拉!」
他們抱著哭泣的我,邊安慰著我,而我心中想著「我好想要趕快好起來」,可是並沒有說出口,因為我覺得我不可以再把這些情緒壓力丟回去給他們,他們已經對我很好很好了,無論未來是烏黑或奶白,我都相信自己是個幸運且幸福至極的傢伙。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