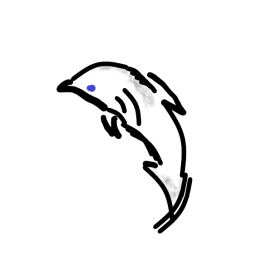說起在瑞德咖啡廳上班的趣聞,倒想起一件。
在距離我們店面斜對角差不多幾十公尺的地方是個小公園,小公園那邊有張稍微掉漆的鐵製椅子,記得前幾個月總有一個看上去挺有型的男生每天上午十點多都會坐在那邊。那個男生看起來不像是沒有工作的人,或說,不像是與都市失去連結的無家者,雖然不可說是穿搭認真,但至少臉貌、跟衣物都是整潔的。
黑色短袖素T、貼身牛仔褲跟一副墨鏡,脖子掛著一支相機,他就是那樣的扮相。
後來我聽老闆說才知道,原來他是滿有名的一位年輕攝影師,去年烏克蘭戰爭的時候他搭飛機到戰地現場,也不管隆隆聲響的砲炸是如此無情,倒也拍攝許多烽火連篇的地獄場景或幾十張尋常百姓的臉龐。長住一個月,攜回數千餘張的電子相片與十數卷底片回台,自費出了本攝影集,名為「生與死」,分兩冊發行,一冊是如紀錄片般如實呈現烏克蘭當地戰爭現況的攝影集,名為「生」,一冊則刻意以搖晃、黑白及粗顆粒的方式冷硬呈現烏克蘭街景的攝影集,名為「死」。
此輯一出,一鳴驚人,
有人讚許他生動紀錄了那些難為他人所見的的角落,
有人則是盛讚他的膽識,認為他竟敢隻身前往「虎山」,
而當然也有那些學者正對於「生與死」這本書的藝術性議論紛紛。
無論如何吧,這本攝影集著實造成海內外許多人的討論,更有出版社有意為其再版攝影輯。
而他從烏克蘭攝影、回台、爆紅之後上過很多YT頻道跟新聞專訪,我對於他一些犀利的論述滿有印象的,多半是針對政治議題所發表許多意見,直白又過度主觀的言論還引起不小風波,但過沒幾個月後他居然就完全消失在螢光幕前,之後再見他就是在這處公園坐著。
這個男生總是一手拿著從便利商店買來的美式咖啡,一手叼著剛點燃的紙菸,
悄悄望著不知何處的遠方,伴著咖啡與菸,是我對他當時最深刻的印象。
而故事的起源,就是這咖啡與菸。
起初發現他出現在公園時,我和老闆都非常驚訝,主動跑去跟他打招呼。可與印象中那些機鋒言詞相比,本人倒顯得扭捏不已,幾乎是不善言詞的,後幾次見著他都是如此,數遍之後,總感覺他不太喜歡陌生人去叨擾,於是我們也識趣的點點頭而已,不會過去說些什麼。
不過他倒有說過一句話,之所以不來我們咖啡廳買咖啡是為了省錢,咖啡廳的咖啡太貴了,
於是老闆提議,如果他來店消費就只賣成本價,不收其他工本費用,因為老闆是他的粉絲,
可是這男生相當客氣,當下點頭稱好,卻一次也沒有真正以成本價喝上瑞德咖啡廳的任何一杯咖啡。
光是這一點,就讓我對他的印象滿好的。
在每天早上的公園裡,見他穿著不合時宜的素T、應該用於低調現在看上去卻異常顯眼的墨鏡、因為秋天來臨的關係而穿上的皮外套,手拿著便利商店買來的咖啡和菸,與旁邊撿拾果實的鳥兒共享著草皮,一旁的榕樹鬚根落於地面,地面都是盤根錯節的樹根像是一面心智圖,從這兒長到那兒去,再從那兒長到這兒來,無邊無盡,無法按圖索驥的找尋到起點與終點,像是混屯的思緒一般。秋風正掃著落葉,枯黃如便條紙般的葉片順勢被風捲起、又落,似乎快樂舒心的隨著氣旋而去,又似乎像沒辦法控制的關係被迫從這兒到那兒去,再從那兒到這兒來。
除了這個男生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大叔會跟著一起出現,
與他不同的是,這一個大叔只會一手拿著保溫瓶,裡頭裝著自己沖泡的咖啡,
另一隻手則是騰出空間拿著手機,播放著不曉得作者是誰的抖音影片,
在那小小方狀的科技產物總發出許許多多嘈雜的罐頭笑聲,像是嘲笑著你我。
這位大叔似乎是那位男生唯一的朋友。身穿不知名的背心,掛著一副粗黑匡眼鏡的他,總是戴著一頂舊舊的登山帽,像極了純粹來公園運動的大叔,誰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位大叔總是能跟那位男生攀談那麼久的時間,兩個人看上去就像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連生活習慣都不同。男生每次都會大叔說,拜託可不可以不要再看那些抖音廢片,但大叔總是呵呵笑說,抖音裡面有很多重要的資訊可以看,退休之後對於世界大事的認識都靠抖音,認為年輕人總是對抖音有過多錯誤的認知。男生每次都聽完大叔的論調都默不吭聲,然後繼續啜上一口咖啡,接著深深吸一口菸,然後深深地吐出去。而這位大叔每次都會在男生吸菸的時候勸告他不要抽太多的菸,免得老了之後容易生病,而男生每次聽完也只是略略點著頭,象徵性點了點菸灰,讓灰燼隨著橘黃色的火苗掉落到地面,直到肉眼難以可見為止。
男生帶的相機是日本出品的「Ricoh」理光相機,
有一次搭上話,我問他,為什麼選擇「Ricoh」而不是其他相機,
他意味深長的看著遠方,像是出神一般望向瑞德咖啡廳的某一處,
然後不知道向是對誰說話般喃喃自語的說:「沒有為什麼,就是為了耍帥吧。」
不過大叔跟公園的鳥都並不怎麼理會相機的品牌,如同這件事從未困擾過他們,哪怕男生有那一天從Ricoh換成Canon,大叔依舊還是會繼續看著抖音,而那些鳥兒也會繼續在土壤旁撿拾掉落的果實來吃,沒有誰會特別在乎這件事,全世界好像只剩男生特別在乎這件事而已。
而在某一天,因為前一天晚上實在是太累了,早早睡去的我當天特別的早起,早到難得可以悠閒地在家邊聽著Spotify推薦的歌單,邊泡著可口的咖啡。剛聽完Joni Mitchell 歡快地唱完「This Flight Tonight」,掛在牆上的時鐘指針像是老闆的叮囑般提醒我該去上班了,才把灑落滿屋的愉悅盡收口袋,把充滿咖啡漬的玻璃杯沖洗乾淨,放回洗碗槽處跟著昨天洗乾淨的碗筷風乾。咖啡廳離我家滿近的,所以我總是騎著單車過去,迎風吹過的街道還是挺好的,雖然仍帶著點車陣的喧囂,至少踩在齒輪上得雙腿還是滿踏實的,大腿每往下一放都證明著「我仍活著」。
騎到附近的公園,熟悉的男生跟大叔同在,男生還是捧著便利商店的咖啡與菸,大叔則是戴著頂登山帽像是給腦瓜子保暖。即便是充滿涼意的秋晨,麻雀群們依然不依不撓的在旁吱吱喳喳的聊著不知什麼的八卦,或許是昨天又看到哪隻燕子不顧孩子的生活去找帥哥,又或者是哪隻八哥竟然再次成功吃到鄰家鸚鵡的飼料。在耳朵叨絮的,除了是麻雀得喊聲以外,大叔跟男生也正在聊天,聊天內容似乎跟前陣子出版的攝影集有關。
大叔喝著他保溫瓶裡的咖啡,對男生說:「欸,小朋友,聽我兒子說,你有出書喔?」
男生喝著他紙杯裝的咖啡,對大叔說:「出什麼書?我哪有出什麼書?」
大叔喔喔喔地叫了幾聲,從他的口袋裡掏出那支每次都用來看抖音的手機,用手指按著螢幕滑著滑著,像是在汪洋大海中找尋著什麼。男生則是一如繼往的看著不知何處的遠方,像是在汪洋大海中找尋著什麼。不出一會兒,大叔「啊呀,就是這個!」的叫了起來。
「這個啊!你看你看!」說著,大叔把手機拿向男生的眼前,如同顯微鏡正在用高倍數看著玻片上的生物,彷彿要男生仔細看清楚每一個線條、每一張紋路。「你的書有在博客來餒,喔~很紅餒,我都不知道。我兒子上次聽我說到你,禮拜六那天特別跑過來看,喔~就說你很紅還怎麼樣的,然後查這個給我看,我才嚇一跳說原來你這麼有名喔,我一開始都不知道你有這麼厲害餒!」大叔興高采烈的這樣說。大叔看上去相當興奮,拿著手機的右臂晃來晃去的,如果他真的是顯微鏡的話那肯定是支架不太穩的顯微鏡。
男生望上去倒是挺冷靜,先是把墨鏡往上一推,瞇著眼睛像是要努力看清楚手機螢幕的成像,然後手一縮,墨鏡又滑落回它應該去的地方,此時男生眼前的景色應該又回歸灰黑色。「攝影集就攝影集,哪有人在說出書的,我才不是什麼作家還是什麼學者有辦法出書勒。」男生低聲說著,幾乎完全不苟同大叔的恭維,而原先推著墨鏡的手仍用食指與中指叼著菸,往嘴裡一送,深深的吸了一口,又往遠離大叔的地方一吐。你幾乎看得出來,雖然男生還是很有個性的做自己的事情,但好像還是會在乎某些人的感受。
「阿呦,我哪知道什麼攝影什麼書的,反正就是很厲害啊!」大叔開心地說著,男生只是微微點著頭,像是不知道可以回什麼,所以隨便做個動作,塞住這個沈默的時間。大叔似乎並沒有發現男生的不回應,依舊像是存在於自己的空間一樣,有著自己專屬的邏輯與節奏,有著自己想要說的話跟想要做的事,於是接著說:「啊聽說你還跑去烏克蘭拍照喔?不是聽說普丁在跟他們打仗?你怎麼還敢過去?你都不怕死喔?」
「怕啊,怎麼不怕,怕死了。」男生如此這般說著。
「怕的話,那你幹嘛還要去?」大叔如此這般說著。
秋風颯颯,是真的發出颯颯的聲響,是風捲樹梢摩擦發出的秋天特有的聲響,風需要稍大、最好還掉落幾片因換季而枯黃得樹葉才顯得更淒涼。麻雀群在一旁仍是吱吱喳喳叫個不停,對於牠們而言,無論戰火如何的蔓延也無論話題如何的蔓延,牠們出現在公園的目的就只是為了生存,得在其他更大的鳥類來搶食之前趕緊把所有的食物吃進肚子裡。而看似與人類親近的鳥兒也與人類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距離,對於牠們而言,無論大叔與男生多麽無害,牠們都只會把人類視作會威脅生命的巨型怪物,稍有不慎便會被擊殺落地的可怕存在,因此,或許某種程度而言,那些吱吱喳喳的聲響也如同在戰地中嚎叫受苦的難民般,發生無奈又懼怕的吶喊吧。
「即便我怕死,我還是想要拿起小刀對這個世界的肉體用力一刺。」
大叔若有所思的看著男生,不確定聽不聽得懂意思。
「我以前很喜歡一個攝影師,他的精神很影響我。在他年輕的時候辦過一本叫做『挑釁』的攝影雜誌,我非常受到那本攝影雜誌的影響,彷彿自己所有的價值觀都被挑釁了一般。於是從此之後,決定非得要做一件非常挑釁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的事情,即便我可能不確定能否成功,即便我可能會就這樣死去,不過我還是想要拿起相機這把利刃,對這個社會惡狠狠地刺向一刀,至少讓這個社會能夠在被某種捏造出來的和平蒙蔽時,可以被深刻的劇痛提醒『我們不可以再如此若無其事地生活下去』。」男生穿著褐色皮衣,再次喝起了便利商店的咖啡,獨有的咖啡香氣跟菸的氣味揉合成某種特殊的味道,戴著墨鏡的他看不出任何的神情,也不確定他究竟是兩眼發光的說著這句話還是兩眼發獃地說著這句話,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大概是我這幾天以來第一次聽到這男生說這麼多話的一次。
秋風颯颯,一旁榕樹得鬚根被吹的像窗簾一樣的動著,隨著幾片落葉的掉落,看起來真是最美的景色。靠海的公園傳了細微的海浪聲,陣陣捲起得海潮拍打在岸邊,擊打著岸邊灰色的水泥堤防。秋陽仍照耀著,但少了夏陽的熾熱,只是緩緩地伸出雙手,靜靜地擁抱著大地。麻雀們仍奮力的用雙腳跳躍,找著藏在雜草邊的小果實,或是躲藏在土壤間的小蟲。
「有用嗎?這樣做真的有用嗎?」大叔邊喝著保溫瓶的咖啡,邊這樣問著。
「不知道,就算沒用我還是想這麼做。」男生邊喝著紙杯的咖啡,邊這樣說著。
「喔喔,那好吧。」大叔把保溫瓶的瓶蓋扭緊。「我已經買書了,中午之後就可以取貨了。」
「你想看就跟我說啊,我可以送你。」男生又是喝咖啡,抽著菸。
「誒,我覺得退休的人不可以佔你們年輕人便宜」大叔推著登山帽如此說道。
「喔喔,那好吧。」男生最後是這樣子回的。
瑞德咖啡廳被秋陽照的光亮四射,招牌反射著白光耀眼無比,透亮的玻璃擋不住陽光,把店內的座位照的是一覽無遺。我把單車牽到咖啡廳旁,從口袋拿出鑰匙開門,回頭望向大叔跟男生,他們又跟麻雀們一如往常地做著同樣的事,麻雀們繼續找尋吃的,他們則是繼續坐在公園說著不知道什麼話語,彷彿這個世界從來都沒發生什麼過什麼事。不過總感覺,確實在男生出現之後,好像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出現,你很難說那到底是什麼東西,也很難說這個東西是否真就造成了什麼了不起的事件。你只能確定的是,當「生與死」發行的時候確實撼動了某些人、某些事,而各大媒體爭相報導這個不怕死的攝影師的各種事蹟,出版社甚至願意為這本自製而限量的攝影集量產,量產到連根本不在乎攝影的人都可以在網路輕易購入。可是當各大通路、各大媒體都開始談論「生與死」時,難道麻雀們便不再找尋果實、男生便不再生活於咖啡與菸、而我便不再來咖啡廳上班嗎?
唯一可以證明的,是男生確實發行了「生與死」,也確實在平凡的日常生活著。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