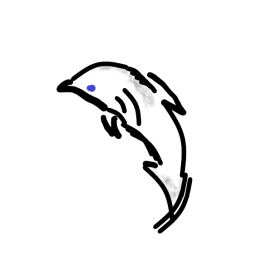他又聽了一次從網路上拷貝下來的自由爵士,廉價的透明光碟隨著按鈕按下後轉動著,勉強還能聽的內建揚聲器發出令人厭惡的扭曲聲響,尖銳混亂的薩克斯風聲宏亮的自那台手提音響炸裂,狹窄的房間內充斥著「Out To Lunch」的音樂。人同專輯之名,短暫的陷入瘋狂,短暫的失去理智,用著已經不太靈光的腦袋撞擊著水泥牆,打著節奏。那台Sony的老舊手提音響是某一日從三重橋下賊仔市摸來的。那天冬日下午,靠近橋下水泥柱旁的攤位擺著各種陳舊的音響、卡帶跟黑膠唱片,層層疊疊的散落各處,一兩名看似老樂友、或可與你伯字輩的親戚年齡相符的老人家正與老闆閒話家常,挺著個大肚子、頂著個黑白相間的頭,操著流利的台語大聲批判共產黨是如何勾串國民黨來搞垮台灣民主。他如一隻老鼠般悄悄的在旁待著,這是他第六週的觀察,假裝來公園運動的民眾,緊盯著攤位各種狀況。
從橋下數來第三根柱子旁賣音響的中年老闆是個囉唆的傢伙,做起事情大擺大闔,看似豪氣實則糊塗,對價格斤斤計較卻對商品管理漫不經心。中午過後約一點二十分左右的時間總會來兩個阿伯跟他抬槓,在空曠的場子大聲喧嘩,吵起架來簡直誇張。某一日,他看到一台黑色小巧的Sony手提音響,那台幾乎被當廢品在賣,外殼有些破損,帶著許多歷史風霜的痕跡,放電池的地方因為嚴重鏽蝕早已不能使用,僅能用電源線供電。按鍵只剩播放可以使用,其他按鈕皆已失效,只有播放CD的功能正常,因為不是什麼經典的機子,所以老闆只在旁邊用白色的紙張草草寫著「900元」,也不怎麼管這台手提音響。
他忽然覺得,這台Sony與他的命運相連,如同偶像劇一般命中注定。
於是他在心中反覆割裂、割裂、割裂著。
那天冬日下午,他約了一個朋友過去,他朋友發覺到他這陣子不太對勁,情緒似乎有點狀況,於是允諾了特地跟他到三重橋下逛攤子。逛攤的他一切如常,也讓他朋友感受到有些放心。兩人步行去附近的攤位吃大骨湯,半大不小的碗公盛著骨頭比肉還多的排骨,蒸騰的熱氣下只是名氣大於口味的普通湯品而已,他的朋友並不喜歡吃這樣的食物,甚至覺得在路邊攤吃這樣的食物有些不衛生,但看著他願意出門走走還是把許許多多的想法吞回腹中。
「我想再去幾個攤位逛逛,看完就差不多可以回家了。」他邊啃著沒什麼肉的骨頭,邊用右手拿著透明塑膠湯匙盛著熱湯喝著,為冷冷的身子增添暖暖的溫度。而橋下的風很強烈,幾乎快要把桌面的醬料碟給吹到地上去,好幾條沒夾好的竹筷塑膠套被吹到骯髒不平的水泥地上,幾隻在偷吃散落在各處米粒的肥碩鴿子對此毫不在乎。
「喔喔好啊,沒問題,你今天狀況還不錯喔。」他的朋友早早就不喝湯了,只是單純把炒麵給吃完。
他們漫步在橋下,四處都是攤販叫賣或人群閒聊的聲音,伴隨著各種鳥叫,簡直是一場聲音的交響演奏會。天空被烏雲籠罩著,陽光被遮蔽住,讓冬日的下午顯得更加寒冷,旁邊的河水總被東北季風吹皺,河邊的芒草如骨牌一般東倒西歪。他走到那處攤販,老闆正在跟幾個中年阿伯大聲爭論著公投門檻降低是不是正影響著台灣未來,那群大腹便便的阿伯義正嚴辭的認為那群屁點大的小朋友根本沒辦法做出正確的選擇,覺得民進黨提出這樣的政策想法根本就是想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著想,完全不顧台灣嚴苛的政治環境,早早就應該讓他們滾下台去。而他的朋友臉色一皺,如同一籠小籠包似的在蒸籠上卷皺著,看上去明顯不喜歡這種大聲吆喝的場合,或者認為這群偏激的老人家政治立場過於迂腐。
而他只是眼睛瞪大的看著那台命中註定的命運手提音響。
在心中反覆割裂、割裂、割裂著。
他伸出手,點了點他朋友的肩膀,悄悄地說:「欸...你...你可以幫我問問靠桌子旁的卡帶能不能單買嗎?他們好大聲好可怕喔,我不敢去問,你可以幫我問嗎?」他手指向老闆腳下的那疊用著破舊膠殼裝著的卡帶,內頁佈滿著霉斑,看上去就沒有被好好的保養著,信手丟在一處,若不是在旁寫著「卡帶出清,一堆200元」,沒人會相信那堆近乎垃圾的東西是商品。
「啊...好吧,那我去幫你問問」他的朋友看上去有些困擾,但還是答應了這件事。
老闆聽到那群阿伯提到民進黨下台怒不可遏,用著比剛剛還要大的聲音反駁,認為他們就是被國民黨的人洗腦,才會說出這種話,提到若不是因為蔡英文的外交政策得宜,台灣早早就在國民黨的政策下被中國吃掉了。他的朋友看起來完全不想要加入那場戰爭,又想著要為他詢問卡帶的事情,只得假裝在看其他的商品四處翻找那些不知名的黑膠唱片,想要等一個合適的時間提問。
偷偷摸摸在旁邊看著黑膠唱片終究還是被老闆注意到了,老闆操著流利的台語說:「欸,同學,你欲愛啥?」。他的朋友像是獲得救贖一般,指向地上那疊卡帶問道:「老闆,這個可不可以單獨買一個就好?」。老闆臉上出現了點厭惡的神情,不耐煩的說著:「單獨買?阿是要怎麼單獨買?200元很俗了拉,欲砍價別來遮看拉!去別攤看拉,麥來家亂拉,擱單獨勒。」說完,老闆朝著他朋友揮了揮手,要對方趕緊滾蛋,別來攤位上問些惱人的問題。
他的朋友小聲嘟囔著:「不賣就不賣啊,兇什麼兇啊?」。說著,轉頭往他那個方向走,誰知道,他早已不見蹤影。
原來,趁著他朋友去問老闆的時候,他如亡命之徒般快速把那台命運的Sony手提音響揣進防風外套裡,因為其他人的注意都跑到他朋友身上,所以沒有任何人發現他做了什麼,而他發現沒人注意之後便佯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的快步離去。他朋友後來打給他問他去了哪裡,他含糊不清的說因為臨時接到重要的電話,必須當下立刻離開,一時之間忘記告訴對方要先走,很抱歉把他留在原處,說是天氣冷了,要對方也趕緊回家。他的朋友雖然覺得莫名其妙,但想著他最近情緒狀況不佳,似乎整個人狀況都不好,即便做出這樣鬼扯的事情好像也可理解,就沒有特別覺得生氣,只是單純留下一句:「好拉,你人沒事就好,處理完事情也趕快回家吧」便把電話掛了。
而他揣著那台手提音響,心臟砰砰跳的,對他而言,他只在乎這台手提音響而已。其實他根本就可以花錢買下這台手提音響,不需要大費周章用偷竊的方式取走它,但因為他認為這是台命定的手提音響,所以必須靠自己竭盡全力的取得,不可以用金錢去做交換,否則那台手提音響便不再是命定的手提音響,而單純只是一台破舊沒用的手提音響,他當時就是這樣思考的。
有人說他病了,他默不做聲,只是在心中反覆割裂、割裂、割裂著。
他特別喜歡日本的戰後文化,喜歡日本戰後那群在藝術方面有著極高成就的音樂家、攝影師、小說家或畫家等等。因此,他得以接觸到各種不同詭異的日本噪音音樂,如惡名昭彰的阿部勳、享譽國際的大友良英等等,他尤其喜歡大友良英組成的自由爵士樂團「Otomo Yoshihide's New Jazz Orchestra」,用筆電反覆播著網路串流的音樂,或是在不知名的外國網站直接下載音樂檔案,拷進光碟內用手提音響來聽,他認為那是人生當中最快樂的一刻,總覺得在孤獨的世界裡被某些人所認識、所接納,對於那些音樂產生了強烈的共情,因而不再哭泣、不再胸悶,如同嬰孩被母親擁懷著,讓狂暴的音牆溫暖而和善的包裹著。
出自於對日本戰後文化的熱愛,他也認識了許多當代知名的攝影大師,其中包括中平卓馬、荒木經惟、森山大道云云之一眾人等,其中最喜歡的攝影師是中平卓馬,認為他的攝影作品極具挑釁性,不僅上網搜刮了中平卓馬的作品,同時也拜讀了他所有中文翻譯的作品。對於中平,他最喜歡的作品莫過於對方在「現代之眼」時期,找來攝影家高梨豊、森山大道,評論家多木浩二及詩人岡田隆彦數人共創發表的三期雜誌-「挑釁」。「挑釁」大大挑釁了他對於攝影的認識,認為原來看似平凡無奇的攝影竟然也能夠如此激進,將時代某個角落推向到另一個階段,這是他特別著迷的地方。除了中平卓馬以外,他也喜歡極為世俗的荒木經惟,認為其荒誕不羈的攝影將女體的性感、魅力、下流、挑逗拍得淋漓盡致,曾有幾次觀覽完荒木的攝影集後因無法克制自己的性衝動,竟還在網路上找外送茶打砲以宣洩自己的情慾。
他其實很討厭不以情感為基礎的情慾,但他還是無法克制那股沒來由的情慾。
有人說他病了,他默不做聲,只是在心中反覆割裂、割裂、割裂著。
而在最糟的那一年,他將二手購入的兩本荒木經惟的「Araki:Tokyo Lucky Hole」攝影集剪成一張又一張單獨的相片,將其從一個整體割裂為數百個個體,接著用麻繩和膠帶將相片黏合在房間的牆面,狹窄的房間被數十位不知名的女體圍繞,而他,也總會在買春的時候詢問對方是否能拍照,並將影像輸出成相片同時地貼在牆上。其中有一張照片,是他上禮拜所拍攝的,照片上是一名看上去年紀差不多落於40-45歲之間的中年婦女,肥碩的乳房上有著一對棕色龐大的乳頭,皮膚因為年紀衰老的關係而有些皺摺,乳房也隨之下垂,之所以會找到她倒不是出於自願,那天,他受到情慾衝動的影響遲遲無法安心睡去,於是他用Line跟幹部溝通後,立即騎車到重慶北路附近一間熟識的越式按摩店買春。由於那天的女生都沒有特別喜歡的,所以頻頻打槍,但不曉得是不是態度有些不佳,反而讓幹部有些生氣,竟然帶著點脅迫的語氣說:「你今天要是不點你就給我試試看。」迫於無奈,他只能勉強自己點一位體型肥胖的中年婦女做半套。中年婦女並沒有那種徐娘半老的風塵魅力,充其量就是個菜市場的大媽而已,這並不是他所喜愛的類型,尤其當她散發的那股體味更是讓他回憶起一些不堪回首的記憶,但是,當中年婦女褪去上衣,露出那肥碩無比的乳房時,他卻覺得有股不可置信的吸引力,看著那衰老的臉龐跟衰老的身體,他的身體竟也不自覺得起了反應,他想起了一些事情,忽然無法克制的興奮從體內竄出,他立即詢問對方能否全套,中年婦女拒絕,但同意在不露臉的情況拍攝,於是才拍下了那張照片。曾有一段時間,他看著那張照片反覆的打手槍,甚至他必須要想起那張照片才有辦法出現生理反應。
他其實很討厭不以情感為基礎的情慾,但他還是無法克制那股沒來由的情慾。
有人說他病了,他默不做聲,只是在心中反覆割裂、割裂、割裂著。
當時的他會把所有想讀的書割裂,將一本完整的書割裂成一頁又一頁的故事,然後從隨機的閱讀中去拼湊出一本書真正想要講的內涵是什麼。他認為唯有這種割裂的方式可以有掌控感,他厭惡一個龐大的敘事,他甚至懼怕一個龐大的敘事,那為使他更直接地意識到自己並不能掌控任何的事情,並連結到一切事情都將失控的聯想,進而引發恐慌症,曾經他因為在學校嘗試讀一篇雜誌的文章導致恐慌症發作而對著牆壁哭了連續四個小時無法停止,之後他的朋友都不敢讓他碰任何的書籍。這種斷垣殘壁式的割裂使他感到安心,他可以在這些短小的語句中得到掌控感,而在他最嚴重的時期甚至需要將一整頁的文字切成數個短而小的句子才能夠閱讀,並配著躁狂的「Out To Lunch」將心靈慢慢沉靜下來。在他過往就醫歷史中,這甚至醫生開的阿普唑侖還要有效,可以從他當時撰寫的片段日記看出某些端倪。
「2021.3.23,天氣」
「晴朗,我討厭寫日記」
「為有股說不出的話想要說出」
「用」
「種方式強烈的不斷的將每一個思緒用」
「它釋放出來,但我還是好怕一不小心」
「失控、失控、失控了」
「3.12」
「頭」
「好可怕」
「好在我還割裂著某」
「東西」
「是我,不是我」
「我覺得很好」
「掌握、掌握、掌握」
「心」
「我」
「病了,想要趕快好」
「討厭自己」
「割裂,我不是我」
他通常會把日記割裂成數個篇章,因為他認為自己也無法掌控自己想要講的話,在他最嚴重的時期,他甚至是不敢說話的。他只能抱著那台命定的手提音響,那是他唯一能夠透過自己努力的方式所掌握著的東西,在他最嚴重的時期,他只能反覆透過播放「Out To Lunch」提醒自己,在這個世界,你永遠不是最孤獨的那一個,這是一種很偏門很自我的一段自我療癒的旅程。在藥物、竊取的手提音響、盜版光碟與一堆碎的不知所云的紙片之後,他才慢慢地恢復為原本的樣子,恢復成他尚且可以稱之為「理智」的樣子,只可惜世界早已跟他所想的不同,所有的一切都被割裂的殘破不堪,他只能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重新找回那些被割裂的片段,比方找到某些除了手提音響外命定的人事物,或成為某種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而之後發生的事情,便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若有時間再寫成另外一篇專欄吧。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