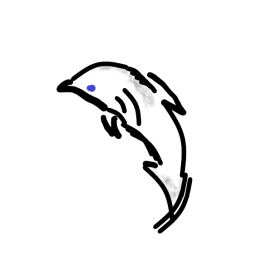龍年:龍,詩一樣的虛實穿梭。早上的報紙副刊串了一串標題,還來不及細看內容就先入主為觀從眼睛裡飛出來一條龍的英姿。數一數龍的爪子,呵呵五指金爪,然確已經人的模樣,甚至更勝一籌人的手腳指掌。難怪,做人的,不一定要先學會怎麼做人,空笑夢什麼時候登龍殿,坐上龍椅,或至少垂聽簾後,母儀天下,還比較接地氣,符合時下。
早起看看早報本就是我不止寒窗十年養成的修為,而今日不是往昔,年假的最後一天,又剛好撞日情人節,雖然已經過了撒狗糧的青春期,好歹一個人的狗窩愛怎麼睡就怎麼個覺,道聽塗說,大爺就是噎大的。誰知道,沒叫雞,雞也叫,春雞報曉,打更的還在放過年假?天罡一勺,在雲鍋子裡端著,雞鳴已經穿腦。數一數雞爪子,不盡人事,偏偏跟我過不去。
說到雞,已經是穿開檔褲時的少年傳奇了。那個時候,宅家屋小,前樑直穿過到了後進,樑下是管事五臟廟的小廚房。灶門旁捐了個小塊地,撓了個五不全小鐵籠,養了一隻骨瘦如柴的小肉雞。雞仔不敏,敏於嘶晨。昔時,大稻埕往西延伸,雖無洛磯山神樣,卻也維持了好長一段時間的西部原始草原風貌。況比今日,已經開墾成了市民大道匝口,名符其實一個雞不能生蛋,鳥已盡弓也藏,偶而還是看得到鳥拉屎的文明之一隅。而家屋雖小,而朔地野大,偶然間家牆外的野地就成了小雞仔放風的好所在。等養了小雞仔初長成,吊起來磅一磅足有三斤十兩重,我拽心肝的寵物雞,老媽眼裡的童養媳,轉個身,一趟水滑洗凝脂,一趟滾水燙雞毛,坐上圍爐的大圓桌盯著看盤子裡陌生的小雞仔眼珠子時,老媽猶自意興風發說她是怎麼拽緊緊雞脖子,斬雞頭的。
小雞仔往生之後,守孝了三年不吃不聞雞肉香,里有雞鳴,不巷歌。直到麥當勞叔叔攻佔了埠頭街角,烤味攤佔盡了黃昏夜市,鹽酥雞搶下了味蕾灘頭堡,這才折軟五斗腰,學人家吃貨,專挑七里香。
久矣夫,少聞雞叫晨。家前面條通馬路快要到土地公廟,大馬路拗了個彎饒下一塊小小地盤,騎車經過壓輪沒注意到,一隻兩隻三隻,五六隻雞突然都飛了起來,那勢頭儼然就是一方惡霸,噴了你一臉雞毛不說,還帶著淡淡的雞大便野之風味。從此,土地公前面的快捷便道就成了生活禁地。至於,雞叫晨,天高皇帝遠,毋擾下民。早上的雞叫聲,是土地公廟那一帶雞角頭叫的吧?是有人在社區偷偷養了個童養媳?是圍爐餐桌上小雞仔的雞頭,老媽拽下雞脖子前,噎了好久,才咯咯咯叫了出來雞叫晨?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