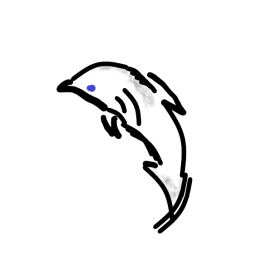夜雨遲來,窗上浹被一層水膜,光牖如洗,窗外的雲襯著些光縫了裙擺,光襯不寂不死,弔詭了春天的早晨。搭高鐵北上,落夜台北地下街北五出口,肩隨的背包沈往下,又提起來,借了把傘穿走在重慶北路一片燈雨裡。讀來的別句串成字串:”別處煙花綻放,此處的午夜/淅淅瀝瀝雨聲寂寞”,字語合膜敲碎手機裡的呼吸聲打亂心跳,等到欺了身近,雨水才涼。涼涼的落雨聲踅亂腳影,止步前面的華陰街少女夢。
阿囡穿的黑裙子搖擺擺走在前面,他盯著眼珠子跟著搖,怕一不小心走失了阿囡的腳印。走過南陽街,站前的忠孝西路浮起一片燈海,招手來揮手去的,過眼即逝短暫的相逢和別離。從臥底公園路轉信陽南陽街角的奧蘿茉開始,玻璃帷幕採光阿囡的裙影,他抓住了,卻不知怎的就墮落了身跟影隨,算不準阿囡什麼時候才來,常常等到了末班車逐塵而去,他才撿起地上的影子恍恍迴光他的腳印。那個季節常常是不喚聲雨水就來,他在季節雨的潰口打水漂一對眼眸,阿囡來了沒來,聽雨聽不到回聲,末班車扯不動塵埃,只是渙散了站前一整條忠孝西路都是車尾燈。
他跟腳阿囡的裙擺伏見南陽街口,穿越過忠孝西路,轉回頭在後火車頭華陰街出沒。季節過後,偶有雨。阿囡女大,他在下游砥石而立,中間風也吹雨也斜,拉出一條雨帶,一把傘遮不住兩個人的天空。漸漸的,天空變了顏色,永夜彷如永晝,華陰街上的少女舖擠成堆他和阿囡兩個人一個影子。阿囡臉上無妝,手袖一條銀鍊子閃閃他和阿囡的手印。直到坊肆通宵打烊了末班車,南陽街吹熄燈號,他看最後一眼阿囡的裙擺,烏漆嘛壓的,無塵室裡,他想要從培養皿拉出一條孢絲,驗證病理。
撕夜的雨破了窗,他忘了阿囡叫什麼名字。
他說不動半個字了,阿囡代言。阿囡在手機裡斷斷續續說話聲:聽說他這樣,就回來了。問阿囡他,阿囡說他還喘著氣。
睡醒了,阿囡就來電話了。問什麼時候來?告訴阿囡現在、立刻、馬上。雨停了,冬去不遠,春天遲到了。
窗外的天空不明不白春天的樣子,這一次北雁南來,再下一次,弄不清楚阿囡是什麼樣子,他的樣子也跟著模糊起來。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