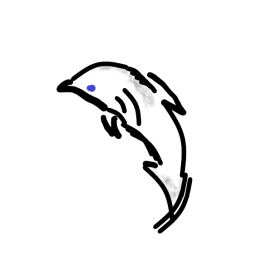失聯了不知多少日子的蘿寄來了一封短扎壓覆在腹黑新細字體的郵簡中。原以為早被判定為植物人的神經性癱瘓,在看到躺在郵箱裡蘿的信簡後突然間像被驟光擊石激活了魚尾,不自覺的整個人都躁動了起來。
早逢其時和蘿,兩個人不打不相識,一次誤打誤撞打出來了兩個人超越性別,堪比石堅的文誼。蘿幼承父教,五歲的蘿天天跟班在國中任教的父親身邊。父親在課堂教課,蘿爬學校圖書館的書架當作是跳房子辦家家,久而久之,醍醐灌頂中西書冊。蘿早慧,受教家學,等到入了小學,平頭齊臉班上同學,一眼就可以找出來蘿。蘿拔了一身青蔥白段清秀模樣,硬是比別人家的孩子高出半個頭,臉色漾光仍不脫稚氣,又泛漾著幾分掖不能藏的性格早熟。
小時候的蘿,是蘿說給我聽的,蘿不會這麼說她自己。但是由小看大,反向推之,從第一眼看到了蘿,就不難想像蘿的孩提時代自是琵琶難掩慧光。其實,和蘿少見,平常的日子裡都是以字代言。但是兩個不擅口沫唇舌的人,一旦上線網路平台,疊字沙推演心思,一來一往目思無暇,忘了是白天還是晚上。蘿精氣神最好的常刻是在午夜。剛交歡了子夜大夢的蘿,甦醒過來,時間準點總會落在半夜一點半不到兩點。不見時差,蘿會先到廚房泡一杯濾紙咖啡,提著杯把走到窗牖下廊郊,打開窗扇,鑿壁月光涓引涼夜,剖書頁漫漫字軌。我總愛說蘿是夜貓子,蘿也總愛說她是在月光底下梳理瓦片的貓。如此自嘲自解。
偶而也會在大白天遇見到蘿。看明晃晃蘿還靜靜的一枝瓶花,好事者以為可以借一碗茶解饞話匣,蘿轉過來梨窩倩笑,不急不緩腳步聲,邊走邊丟下話:上課去了!而此時向外望出窗台,對街的國中校園正好到了下午最後一堂課,正課無聊,操場上滿是各擅勝場的籃足排球。憑望時,窗台上依稀還殘放著蘿倚袖當年留下來的淡淡的咖啡香。蘿說過,當年穿堂風穿過大學穿堂,舉球員、大砲手在穿堂旁邊的草地上走位練場,夏灩蒸風猶似在蒸汽房裡蒸毛細孔,汗浹雨背弄濕了頭髮。蘿摘下掛在頸肩上的毛巾,用力一抹,額汗依舊滴著,擰一把毛巾擰滴在草地上,讓一地的韓國草揹了一身鹹濕。
蘿騎單車縱走北海岸,沿途淡金公路總也不忘留下蘿的身影。蘿還是唸碩士班時的打扮,輕裝簡著,脖子上掛一條毛巾。少年狂狷,少女含羞,蘿站著歪身靠在野柳石巖的照片丰姿綽約,寬沿大帽子、太陽眼鏡遮蔽了風華,求一反三,追問下,才知道是蘿家裡養的兩隻蠶甬正在作祟青春。典當歲月,賒了幾文錢青春,青春不早還,同窗依舊在。當年的鯨面女孩,大學的閨蜜,邀了一起上台北置辦女兒嫁衣。一行四人借步和平東路最後一抹霞色,濯韶影躑躅蒲葵林,聊八卦復古少年。直到天色晚了,拍碎翦影,離別了心房,醉歸鳥巢。
蘿不姓羅,也不鯨面,頂了個小個頭就隨著父親渡海來台,落腳台東太平溪畔,在學校圍牆外的新生路巷子租了一間小房子,騎牆蘿的少女時代。長大了,蘿賃屋住在師大路上的隔間套房,臍帶父蔭,學父親誨人不倦的孜孜風範。直到自己也拗斷了不知多少根粉筆頭,寫下多少年的黑板字,才萌生退意,甘心做一隻抱夜毬梳理月光的夜貓子。我問蘿,蘿的玫瑰來自後山?蘿定義她的玫瑰:嚴格說來,玫瑰是生養在撒哈拉的玫瑰。就像蘿漂移的足跡,踮腳撐起來小個頭大眼睛趴在船舷上看一波波海浪騷動星星的方位,坐火車穿山洞輕一身的黑裙子白襯衫霪雨瓜皮,留長了剪短了髮戴養她的蠶寶寶。見到蘿的時候,有人告訴蘿,蘿轉述給我聽:重要的東西,是眼睛看不到的。
收到蘿寄來的最後一封信,蘿已經別了身影,只說這個時候皇后區第五街的櫥窗映雪,雪地上,是奧黛麗赫本踩雪靴留下來的雪印。
還沒打開蘿復出後寄來的短扎,蘿要說的是什麼重要的東西?還是眼睛看不到,但是心裡很清楚,那些不曾說的,在鴻飛之際,不小心也留下來了腳印。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