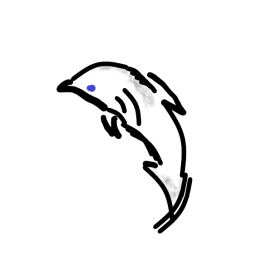年初五的早上,幼華傳賴說,正從泰安鄉梅園部落拔杉而下,背景山嵐雪見,日曦逐雲而上,兩隻腳正在疾走紅塵。說是如往昔那般的,散了不見,不見了一別兩歡,酒凝的文字才是彼此的歡場。沈酣了一夜沒給幼華回訊,立春一早,走到陽台先讓冷空氣洗了一把臉,繼又用熱水敷面,俟酒醒的瞬間,文字還在熱身,只回了幼華一句質性歇後語,不關時間空間的問話:“人呢?”
人呢?幼華偶發性的一句問話掛在賴上,卻是幼華此刻最最溫柔。至少,聽了會以為弦外。代價是擺渡了時間,陌生的別刻,一張倉鼠的臉。常常都是這樣,倉鼠掛牌上市,我的臉已經貼作壁紙。年前就走失了幼華,召回的訊息掛在認領處久久仍不待見。一事經二不經三,等把心情做成死會,顧不旁他,只好玩玩拆字拼圖遊戲,撇眼,幼華蹴地躍上版面,丟給一句:“在!”圖文並茂,幼華給的是一張大宇宙小行星全人風景照,照片中幼華面冷,光害搶了主人翁臉部表情,看不清楚誰誰,反倒是陪襯的阿貓阿狗表情豐富,喧了賓也奪了主。問幼華:“爾等?”讀幼華的回訊,不知道幼華什麼臉,卻似聽得到幼華的噗笑聲:“君不見,我單身,我不公害。路人甲乙而已。”想到了什麼反問幼華人呢?每次都會有種看正臉不如猜幼華背影的感覺。至少,幼華的背影很真實,很夠份量猜想。
幼華少言,聒噪起來的時候就是一片文字海了,聽者棹楫孤舟,隨時有覆舟滅頂的危險。就像是脫軌時代裡的許可,從善之,如流由她,在語言的尖峰底下不要做一隻挨打的雞蛋。而做軟骨頭但不折腰,又是和幼華經過多少次矛與盾的交鋒後,始萃然於心。
實價登錄後,愛情變得越來越廉價了。想當初,及至現在,我和幼華情文並茂書裡,卻有著不說的秘密:“我可能不會愛你!”當嗜酒一杯,夜又寂時,醉後醒來躺在身邊的人不是你。就像幼華一時興起貼的符咒:“你做的春夢,不是我的人。”然而,我做惡夢的時候卻常常有你。
我們都說,這樣也好!想當初,及至現在,和以後的未來,不懸心執子之手,但懸念誰的背影什麼時候也長出來了白頭髮?
上一篇 下一篇
Copyright © www.penpal.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Penpal筆友天地
以上內容皆由各著作權所有人所提供,請勿擅自引用或轉載,並僅遵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 若有違相關法令請<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我們將以最快速度通知各著作權所有人且將本文章下架,以維持本平台資訊之公正性及適法性。

top↑